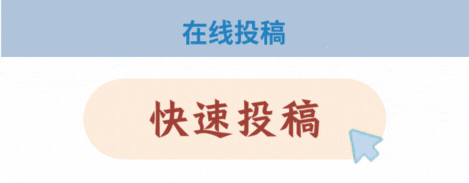文化专有词在文学作品中的翻译与诠释—以鲁迅的《祝福》中“祝福”一词为例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处处呈现或隐或现,半隐半现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信息”。要理解这些文化信息,就要进行文化解码;很显然,如果不能解码或者解码出错,就不能准确的理解原文。正如Juri Lotman所言[1],“没有一种文化不是根植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结构为其中心的。”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多姿多彩[2],跨语言文化交际则要穿越差异。这就要进行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求同存异,一同释义,或原原本本摆出差异后再求理解;并在穿越差异中加强不同语言文化的交往与相互理解[3]。
“文化专有词”,又称“文化负载词”或“词汇空缺”,指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地理因素,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4],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烽燧习惯和文学艺术等,这使得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载语言和词汇的使用上产生了差异,进行形成了各具特色化专有词。因其通常只存在于某一种文化中,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是空白的或难以找到对应词,因此为跨文化交流和翻译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一般认为,“概念史”一词最早见于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论部分,而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概念史肇始于二战后的德国,应“语言学转向”而兴起,而后受到“文化转向”的影响。不同于传统史学研究以人物、事件为对象,概念史将概念作为专门的历史单元,研究概念在时空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容受和扩散,通过分析重大历史转型时期的政治和社会“主导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以揭示历史变迁的特征[5]。目前已有翻译学者(屈文生,2012; 刘瑾玉,2019) 将视野投向概念的译介及其本土容受过程,胡开宝则更是将翻译概念史( history of translated concepts) 视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定义其为“从历史维度分析外来概念的翻译及其译名的演变,考察具体外来概念在目的语语境中落地、协商、生根和变形的研究”,并置于数字人文的视域中系统论述中国翻译概念史的研究内容、特征和路径[6]。
在《祝福》英译本的研究方面,目前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对于其中的“祝福”一词的英译,学术界也没有进行过详细的研究。本文将对各译本中“祝福”一词的翻译,先进行源语语境的文化含义的探索,以各英译本出版时间为线索,进一步分析各英译版本中“祝福”一词的翻译所蕴含的深刻内涵,从而为文化专有词的翻译研究提供有益参考,为翻译概念史的研究提供具体案例支持,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交流,同时也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
1 《祝福》及其英译历程
在《祝福》中,叙述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教和迷信对底层人民的压迫和摧残,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小说也阐述了像文中的“我”以信仰的启蒙知识分子,对当时人们自私自利以及世态炎凉的这个社会现状的无动于衷和不知所措。
自 1924 年《祝福》发表后,它得到了很多著名翻译家的欣赏,迄今为止共有6位译者英译了《祝福》。按译本出版的时间先后分别为: 斯诺和姚莘农合译的“Benediction”(1936,以下简称“斯译”) 、王际真译的“The Widow”(1941,以下简称“王译”) 、柳无垢译的“Benediction”(1946,以下简称“柳译”) 、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The New Year Sacrifice”(1954,1960,1972,1980,以下简称“杨译”) 、莱尔译的“New Year’s Sacrifice”(1990,以下简称“莱译”) 和蓝诗玲译的“New Year’s Sacrifice”(2009,以下简称“蓝译”) [7]。其中,“柳译”本和“斯译”本的译文完全相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杨宪益夫妇对他们1954 年所译的译本进行了三次修改,即1960年、1972 年和1980年。1980年版的译文改动最大,几乎接近重译。因此,本研究用的“杨译”本是其1980年版的语料[8]。
2 “祝福”的文化内涵
《祝福》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深刻揭示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小说,其中的“祝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2.1 作为习俗的“祝福”
“祝福”在小说中首先指的是旧时江浙一带每年年终的一种习俗,人们通过祭祀来祈求来年的好运和幸福。这一习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神灵和祖先的敬畏以及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在小说中,祥林嫂的生活被笼罩在这种“祝福”的氛围中,她和其他人一样,都希望通过祭祀来祈求好运和幸福。然而,这种习俗背后却隐藏着封建礼教的残酷和冷漠,祥林嫂最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祝福和幸福。
2.2 作为反讽的“祝福”
鲁迅先生巧妙地运用了“祝福”这一习俗,将其作为反讽的对象,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残酷。小说中,祥林嫂在众人祝福之俗中投水而死,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使得“祝福”这一习俗在小说中具有了深刻的讽刺意味。它暗示了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以及人们在这种礼教下的无奈和悲哀。这种反讽手法的运用,使得小说更加深刻和引人深思。
2.3 作为命运的“祝福”
“祝福”在小说中还代表着一种对命运的无奈和妥协。祥林嫂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悲惨和无奈,她不断地努力着,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最终她却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走向了死亡。这种命运的无奈和妥协也是《祝福》中重要的主题之一。小说中的“祝福”氛围与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凸显了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摧残和压迫。
小说中多次描写了祭祀的场景,如人们忙碌地准备祭祀物品、祭祀时的庄重氛围等。这些描写不仅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还为后文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当祥林嫂在众人祝福之俗中投水而死时,这种祭祀场景与她的死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使得“祝福”这一习俗在小说中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综上所述,《祝福》中的“祝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呢,它既是习俗的体现、反讽的对象,又是命运的象征。这些内涵共同构成了小说的深刻主题和引人深思的艺术效果。
3 译者简介
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的过程中至关重要,阐释学认为文本意义在阐释中生成变化,译者作为主题,其对原文的理解,解释和再创造的主观能动性直接影响译文质量。
斯诺是翻译鲁迅文学的第一位美国人。他认为,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他认识“旧中国的现实和新中国前景的开端”。他相信翻译新文学的优秀作品能“帮助我们了解正在改造着中国人的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及文化的力量”[9]。斯诺的选集《活的中国》中,收录了30部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这将是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选集。鲁迅和茅盾,这两位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鲁迅作品最终入选7篇,而非6篇,且并非全部出自《呐喊》,而是3篇选自《呐喊》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2篇选自《彷徨》集(《祝福》、《离婚》),另有2篇分别选自杂文集《坟》(《论“他妈的!”》)和散文诗集《野草》(《风筝》) 编译选集之初,斯诺与姚克结识,邀请他一起合作[10]。姚克是苏州东吴大学的毕业生,虽然没有出过国,但英语十分纯正、地道,而且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均有较深的造诣,是难得的翻译合作人选。更难得的是,合作者姚克对鲁迅仰慕已久,对编译计划显示了浓厚的兴趣。
本文第二个英译版的译者是美籍华人学者王际真,她对鲁迅在英语世界的推介起着重要作用。她敬仰鲁迅,认为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人物”[11] 。学者王际真也将部分鲁迅小说译成英文,在上海的《天下》(T'ien Hsia)月刊及美国的《远东》(Far East)杂志陆续发表,这些译作于194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结集成书,题名为《鲁迅选集》,成为英美出版界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鲁迅小说集。王际真译本出版后曾获得美国媒体广泛关注,但囿于政治局势骤变和中美文学传统差异,译本传播范围有限。
国内翻译泰斗杨宪益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祝福》,并先后三次进行修改,在国外皆获得好评,产生了广泛影响。他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信、达、神韵”的翻译原则。他说:“‘信’和‘达’在翻译中缺一不可,要做到‘信’和‘达’兼备是不容易的事。总的原则,我认为是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加或减少。但实际做起来,要忠于原文,又要表达原作的神韵,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杨宪益对其译作进行精雕细琢[12],并对对同一部作品进行多次修改,只是为了使翻译作品尽可能地还原出原作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直至达到“信、达、神韵”的水准。
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是一位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和翻译家,他在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对于鲁迅先生的作品,莱尔展现出了深厚的理解力和翻译才华。莱尔认为“译者要提供足够多的文献资料以确保读者对文本能有大致相同的理解”[13]。他的翻译工作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还加深了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英国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起到了重要作用。她认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并不亚于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她受企鹅出版社邀请翻译了鲁迅小说,尽量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翻译鲁迅小说,目的是要把鲁迅在中国的经典地位介绍给普通的英语读者,让他们了解到“鲁迅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观超越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14]”。如何全面把握鲁迅作品中的中国历史背景,深入理解中西文化中的差异,使译本既具优美感,又能忠实表达原文,是蓝诗玲所面临的挑战。市场的反馈也没有辜负她的努力,她的译本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被誉为是所有译本中“最可读易懂的”。就这样,中国文学终于走进了西方主流的图书市场,鲁迅的作品也走向了更多外国读者。
4 案例分析
文化专有词是在特定文化中产生的,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词汇。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文化中独有的事物、概念、观念等内容,在其他文化中可能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来精准翻译。例如,“功夫”这个词源于中国武术文化。它不仅指武术技能,还包含武术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如坚韧、自律等精神品质。下面逐一分析《祝福》各译本中“祝福”一词的翻译。
小说题目《祝福》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祝福”作了两条释义:①作为动词,原指向神祈福,今指祝人平安和幸福;②作为名词,指除夕祈求天神降福的旧俗[15]。这是“祝福”的概念意义。小说中的“祝福”包括了“祈求天地神灵祖宗赐福”,也包括了“祝福”用的“福礼”。这指的是“祝福”的文化内涵“过年前的家庭祭祀”。
五位译者分别将题目译为:
斯译: Benediction
王译: The Widow
杨译: The New-Year Sacrifice
莱译: New Year’s Sacrifice
蓝译: New Year’s Sacrifice
分析:
1. Benediction(斯译):这个翻译偏向于宗教或神圣意味的“祝福”。然而,《祝福》虽然涉及年终祭祀和祈福的场景,但其主旨更多地在于揭露封建礼教的残酷和对女性的压迫,并且汉语“祝福”无宗教概念意义。因此,这个翻译丢失了部分文化内涵,无法全面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主题。
2. The Widow(王译):此翻译聚焦于小说中的主人公祥林嫂,她是一个寡妇。然而,将题目翻译为“寡妇”过于简化了小说的内容,忽略了小说中丰富的社会背景、祭祀场景以及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这个翻译虽然突出了主人公的身份,但未能全面反映小说的主题和情节。
3. The New Year Sacrifice(杨译):杨宪益及其夫人的翻译都选择了“新年祭祀”作为题目的翻译,这个翻译准确地捕捉到了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年终的新年祭祀活动。同时,“sacrifice”一词也隐含了祭祀活动中可能包含的牺牲和悲剧意味,与小说主题相契合。因此,这个翻’既体现了小说的文化背景,又暗示了小说的主题。
4. New Year’s Sacrifice(莱译和蓝译):莱译和蓝译与杨译相似,都强调了新年祭祀的元素。然而,莱译、蓝译在语法结构上略有不同,将“New Year”作为名词所有格形式,与“Sacrifice”相结合,强调了祭祀活动是与新年紧密相关的。这种翻译方式同样能够准确地传达小说的文化背景和主题。
综上所述,对于《祝福》题目的翻译,The New Year Sacrifice和New Year’s Sacrifice更为贴切和全面,它们既体现了小说的文化背景—新年祭祀活动,又暗示了小说中可能包含的悲剧和牺牲意味。而Benediction和The Widow则相对较为片面或简化,无法全面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主题和情节。
5 结语
在《祝福》这部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小说中,“祝福”一词承载着丰富的意义,包括作为习俗的年终祭祀、对封建礼教的反讽以及对人物命运的象征。通过对六个不同英译本中“祝福”一词翻译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译者在处理这一文化专有词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各有千秋。
斯诺和姚莘农合译的“Benediction”在题目翻译中虽传达了一定祝福之意,但因偏向宗教意味而未能全面体现小说揭露封建礼教残酷的主旨;王际真译的“The Widow”聚焦主人公身份,却简化了小说丰富内容。而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The New-Year Sacrifice”、莱尔译的“New Year’s Sacrifice”以及蓝诗玲译的“New Year’s Sacrifice”在体现新年祭祀文化元素方面表现出色,且后两者在语法结构上强调了与新年的紧密联系,更贴合原文文化背景和主题。
翻译概念史在《祝福》不同英译版中扮演着多方面的重要角色,它犹如一条隐匿的线索,贯穿于各个译本的生成与演变过程之中,深刻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对原文文化内涵的理解与传递,以及译本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功能与价值。
翻译文化专有词时,译者需要充分考虑原文的文化背景、主题思想以及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既要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又要使译文在目标语中通顺易懂,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祝福》中“祝福”一词在不同译本中的呈现,也为文化专有词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1]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9.
[2]Aísa R ,Cabeza 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defining the retirement pattern[J].Research in Economics,2025,79(3):101062-101062.
[3]徐钧.翻译思考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4]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5]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编),新史学(第三卷)[M],北京: 中华书局.2009.
[6]胡开宝.数字人文视域下现代中国翻译概念史研究—议题、路径与意义[J].中国外语2021(01):10-11.
[7]杨坚定,孙鸿仁.鲁迅小说英译历程及展望[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04):49-54.
[8]杨坚定.《祝福》五个英译本的文化专有词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语篇分析[J].上海翻译,2018(2):63-68.
[9]王鹏.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翻译活动[J].上海翻译,2002(3):39-41.
[10]许磊.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1]王际真.鲁迅选集[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9.
[12]杨宪益.去日苦多[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
[13]Han Q ,Li C ,Jin Y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terprise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25,105 104179-104179.
[14]覃江华.蓝诗玲的翻译观及其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J].中国翻译,2010(6):117-121.
[15]李行健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李君芳,女,汉族,河北唐山,华北理工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