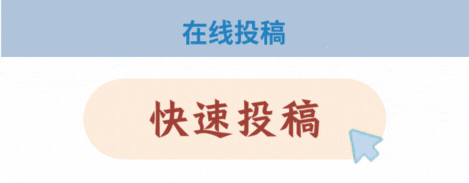白字戏中小生角色的塑造规律与艺术表达
引言
作为国家级非遗剧种,白字戏以浓郁的地方色彩、典雅的唱腔和质朴的人物塑造,在南方戏曲中独具特色。小生行当不仅是情节推进与情感表达的核心角色,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象征意义。然而,面对当代观众审美的变化,传统小生表演程式与现代表达之间出现张力。演员既要继承传统技艺,也需探索创新路径以实现艺术重构。本文聚焦小生角色,从类型特征、塑造规律、表演形式和当代表达四方面进行探讨,旨在为白字戏的传承与活态发展提供思路与支持[1]。
1 小生角色的艺术特征与类型划分
1.1 白字戏小生的艺术特征与表演定位
白字戏小生行当在剧种结构中独具分量,是传情达意的核心角色,承载着观众与剧情之间的情感通道。从艺术特征角度分析,白字戏小生不仅要“形俊”“神清”,更要具备文雅中带有书卷气的气质表达。在形体语言上,小生讲求挺拔的身姿与柔和的动作结合,眼神中要体现出人物的含蓄、深情、谦逊与从容;动作不宜过猛,步伐讲究“碎而不乱、稳中带捷”,充分体现出传统士子温文尔雅的美学意象。在声音方面,小生所用唱腔偏于细腻清亮,音域不高却极富韵味,讲求用真嗓和假嗓结合,或低吟或婉转,以达到抒情写意、以情带声的艺术效果[2]。
这一行当还具有极强的戏剧功能,其角色多为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因而必须具备全面的表演能力,包括对节奏的精准把控、对白与唱段情感的自然过渡以及与其他角色之间的互动应对。小生角色常见于表达爱情、忠诚、才学、忧愁等主题的剧目中,如“才子佳人”“志士忠良”“书生行侠”等不同情节架构。因此,小生演员需在演技中兼具“文功”与“武技”,既要有细腻的心理刻画,也要有熟练的身段动作。尤其在白字戏这种较为写意、节奏缓慢、重唱轻打的剧种中,小生的台步、手眼身法等细节处理更为关键,其表演是否自然、精准、富有节奏感,直接决定了该角色的可信度与吸引力[3]。
1.2 典型小生类型及其舞台呈现特点
白字戏小生的分类依据角色设定与人物身份,可分为正生、穷生、风流生、武生等几类,每一类在塑造方式上各具侧重。其中,正生是最为常见的类型,常为忠良之士、士子书生或正义官员,形象端庄、仪表清朗、语言典雅。他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偏重于抒情与正面表达,表演以稳健、含蓄为主,唱腔平稳流畅,表情细腻内敛,充分体现儒雅正直的精神气质。而穷生则多见于描写社会底层知识分子或遭遇不幸的青年,形象略带落魄,演出时注重展现角色的内心苦楚与人情悲凉,唱腔略带忧郁,身段也更显疲态,以唤起观众的同情和共鸣[4]。
风流生与武生则呈现出更为丰富与多元的表达方式。风流生往往具备较强的表现力,形象潇洒俊逸,举止风趣灵动,是白字戏中带有调侃与喜剧色彩的角色之一,需通过精准的语音处理、身段张力与轻松的台步节奏来塑造角色的多情与机敏。而武小生则多在涉及动作场面的剧目中出现,强调身法与武技,需完成跑圆场、跃步、亮相等繁复身段,并在唱腔中加入气声与顿挫的变化,形成一种刚中带柔、文武结合的舞台表现力。以上这些分类不仅丰富了白字戏小生的表现层次,也对演员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只有准确理解各类角色的文化属性与心理背景,方能在舞台上呈现出具象而立体的艺术形象[5]。
2 白字戏小生形象塑造的基本规律
2.1 角色性格建构中的情感逻辑与行为动因
白字戏小生形象的塑造,并非仅依赖外在的身段与唱腔,而更深层地体现在对人物性格、情感状态与行为逻辑的建构上。优秀的小生表演者不仅要完成人物“像”的表面呈现,更要深入人物“神”的塑造。这就要求演员必须从文本出发,理解角色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结构、身份地位和心理情绪等多维因素,并据此做出符合逻辑的情感设计与行为表达。比如在表现一位忠贞不渝的书生时,演员在语调控制上要体现坚定与节制,在动作安排上需展现出克制、内敛的特点,从而贴合“忠君报国”或“守节思恋”等传统伦理情境。
同时,白字戏强调“以情动人”,小生作为最具抒情色彩的行当,其角色情绪通常较为丰富,起伏也更显复杂。演员需要掌握情感推进的节奏感,避免“平铺直叙”或“过度渲染”。例如在表达由喜转悲、由羞至怒的情感变化时,需通过肢体微调、面部细节及唱腔层次的处理,使观众自然接受角色心理转变,从而在情感上与角色产生联结。这种“情感逻辑”是小生塑造的核心规律之一,它决定了角色的真实感与感染力,也对演员的理解力与表现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将角色动因与舞台节奏完美结合,才能真正打动观众、提升表演质量。
2.2 程式化与写意化结合中的艺术技巧
白字戏作为南方典型的写意戏曲,其小生表演程式以“意在形先,情动形随”为核心理念。在角色塑造过程中,演员通常不追求现实主义的细节复刻,而是通过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语言与典型化的情绪表达,传达人物的内心活动与社会角色。例如,拱手、捋须、转身等看似简单的动作,在不同语境中承担着完全不同的象征意义。小生演员要根据剧本与语境变化,灵活使用这些程式,同时保持动作的美感与节奏统一,以完成舞台上有限空间与无限情感之间的艺术转换。
在程式之外,写意则提供了小生形象塑造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比如角色在表达情爱、离愁、忠义等情感时,往往不是通过直接陈述,而是借助虚拟动作、象征唱词与意境营造进行间接表达。在这方面,小生演员需具备较强的舞台“留白”能力,即用有限的语言与动作,启发观众在脑海中“补全”故事的情境与情感。这种艺术处理方式既要求演员具备深厚的传统程式基础,也需具有高度的情感控制力与舞台感知力。程式化是根,写意化是魂,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白字戏小生角色塑造中的核心技艺与规律路径。
3 表演技艺中的艺术表达方式
3.1 唱念做表中的细节展现与情感传达
在白字戏的表演体系中,“唱念做打”是四位一体的艺术基本功,而小生行当在这四方面的技艺要求尤为严格。首先,“唱”是表现情感的核心手段之一。小生的唱腔讲求清润、灵动与韵味,注重气口平稳、吐字清晰与转音细腻。传统白字戏常采用高腔、平词等唱段,唱腔结构层次分明、节奏悠缓,特别适合抒发小生内心的愁绪、忠诚或爱恋。在演唱过程中,演员需通过对腔调的轻重缓急、虚实强弱的把握,使声音与情感紧密结合。尤其在情绪爆发点,需将真假嗓自然转换,形成既具张力又不失柔和的听觉效果,使观众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情感波澜。
“念”则承载着对白中的节奏感与表达力,是连接唱与表的重要纽带。小生的念白风格偏向文雅、节制,讲求语速稳健、语气亲和。演员在念白时需注重抑扬顿挫,结合角色心理变化调节语调,例如在表达感伤、纠结等情绪时,使用略带哽咽的“低语”,既展现人物内心矛盾,又增强观众的情感代入。在“做打”方面,小生强调手眼身法步的细腻统一,尤其手势、眼神和步伐的协调尤为关键。例如“一顿步三分情”,通过有节奏的移步和手部开合,可精准传达角色的身份、情绪与心理状态。整体而言,白字戏小生通过唱念做表的高度配合,构建起富有层次、真实动人的艺术形象,形成强烈的舞台表现张力。
3.2 身段语言与角色情境的融合表达
身段作为戏曲舞台表演的核心语言之一,是小生角色艺术表达的外化载体。在白字戏中,小生的身段语言尤以“含蓄”“自然”与“节制”著称,其基本要求是动作必须源于情感,而非为程式而程式。举例来说,小生行礼、执扇、抚琴、读书等常见动作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强烈的身份意识与情境暗示。例如一个转身动作,如果搭配愁绪的音乐与微蹙的眉眼,便传达出离别的痛楚;若是加以轻快步伐与仰首神态,又显出风流自得之情。因此,小生在身段上的把握不能流于机械模仿,而要通过微妙的节奏与力道调整,实现“意中有形、形中见情”的艺术效果。
此外,白字戏重视“程式中的写意”,这使得小生在身段表现上具有较大的创造与延展空间。例如同样是上楼动作,演员不会直白地“走楼梯”,而是以“云手—抬步—回身”一套程式化动作,借助虚拟与象征,引导观众完成视觉与空间的“脑补”,从而达到情境共鸣。更重要的是,演员在具体表演中必须根据剧情推进与人物关系变化,动态调整自己的身段策略。特别是在面对多角互动、转场切换等复杂情境时,小生需具备极强的空间感与节奏感,才能既不破坏舞台结构,又保持角色完整性。这种“情境—角色—动作”三者统一的表达方式,正是白字戏小生表演艺术最具魅力与难度的体现,也正是其艺术传承与创新的关键所在。
4 当代表演视域下小生塑造的传承与创新
4.1 面对现代观众审美的转变与表演调整
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演变与观众结构的多元化,当代戏曲观众在审美心理、情感节奏及接受方式等方面已发生显著变化。白字戏作为地域性强、语境密集的传统剧种,其小生角色若仍固守旧有程式而缺乏现实感知,容易被年轻观众视为“抽离时代”的存在。这种脱节在语境、节奏与情感传递等维度表现尤为明显。例如传统小生唱腔中长篇念白、层层铺垫的结构,虽然富有节奏美,但对快节奏接受习惯的观众而言可能形成审美疲劳。因此,在当代表演中,演员不仅要坚守传统程式,更需对表演节奏、唱词表达与情感传达方式做出适度调整。
具体而言,白字戏小生在表演节奏上可以做“减法”,突出关键动作与核心唱段,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与冗余。在唱腔处理上,保留原有调式风格的同时,适当融入情绪递进、节奏变化或现代音响设计,以提高观赏体验。在情感表达方面,应强调真实与自然,弱化“高腔喊唱”式的过度渲染。例如在表达书生内心挣扎时,可用轻柔的吐字、细腻的面部表情和节奏缓慢的身段配合,拉近与观众的情感距离。更为关键的是,演员需深入理解当下观众对“真实”的认知和期待,通过情理逻辑与戏剧张力的双重锤炼,使小生角色既保留传统美感,又具备现代观众的共鸣点,从而实现与观众的“共情”而非“隔世”。
4.2 传承路径中的青年演员培养与剧目创新
白字戏小生艺术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系统化的传承机制与创新能力的融合共进。在人才培养方面,当前存在“老一辈渐退,新生代断层”的现实困境。由于小生表演难度大、训练周期长、舞台积累慢,许多年轻演员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系统指导,或仅掌握“技”而未能体悟“神”,难以完成角色的精神重建。因此,建立校团联合培养机制、加强传统程式与文化素养的同步教学,已成为传承工作的当务之急。此外,应鼓励老艺术家以工作坊、传帮带等方式,将自身经验口传心授,并注重将理论转化为具象范例,使青年演员在演中学、学中演,逐步掌握小生塑造的核心规律。
在剧目内容与表现形式上,白字戏亦需走向“守正创新”的路径。一方面,应继续发掘传统剧目中尚未开发的经典文本与小生核心段落,注重版本整理与舞台复排,保持剧种的传统根脉不被湮没;另一方面,也应尝试在新编历史剧、现实题材戏中大胆赋予小生角色新的表达空间。如将传统才子形象与现代知识青年的责任意识融合,通过情感、身份与时代的交错表现,展现具有时代张力的新型小生形象。此外,借助多媒体舞台、数字投影、现场配乐等手段辅助表演,也为小生艺术提供了拓展表意空间的新契机。在传承与创新的动态平衡中,小生作为白字戏的灵魂角色,将更有可能以“活态”形态继续被观众接受与欣赏,推动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实现有机更新与深层融入。
结论
白字戏小生行当作为戏曲艺术中富有表现力与文化内涵的重要角色类型,其塑造规律体现了传统美学与地方特色的高度融合。从角色特征、艺术技艺到情感表达与当代表演适应,小生不仅承载了剧种的精神气质,也成为戏曲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支点。面对当下观众审美的转变,唯有在坚守传统表演技艺的基础上注入现实关怀与艺术活力,才能实现白字戏小生从“传承”走向“生长”的实践跃迁,助推地方剧种持续焕发时代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邱燕红. 白字戏的艺术特点及传承创新策略[J]. 新传奇, 2024, (41): 92-94.
[2]温和. 从《山伯访友》的“音高困境”看潮音戏的童伶音区[J]. 中国音乐, 2024, (01): 99-108.
[3]朱碧茵. 白字戏剧目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思考[J]. 剧影月报, 2023, (03): 30-32.
[4]吴庆坚. 论白字戏舞台表演艺术与创新[J]. 大众文艺, 2019, (12): 137-138.
[5]钟静洁. 白字戏的传承与发展探索[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18, 2 (21): 79+81.